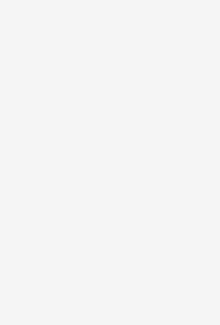何处安放你藏起的笑容? 超清
分类:纪录片 地区:法国年份:2001
主演:达尼埃尔·于伊耶,让-马里·斯特劳布
导演:佩德罗·科斯塔
更新:2023-06-27 15:29
简介:这是佩德罗·科斯塔(PedroCosta)的另一部伟大的电..这是佩德罗·科斯塔(PedroCosta)的另一部伟大的电影,讲述了两位导演(DanièleHuillet和Jean-MarieStraub)之间的关系,他们试图剪辑电影《西西里岛!».在这个过程中,斯特劳布和惠利特在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中谈论了电影... 译自https://www.diagonalthoughts.com/?p=1814 佩德罗·科斯塔与汤姆·安德森就丹尼埃尔·于伊耶与让-马里·斯特劳布夫妇的对谈。对谈发生于2006年9月28日加州艺术学院Bijou放映厅《何处安放你藏起的笑容?》映后,最早发表于Cinema Scope2007年冬季第29期。 —————————— 《没有秘密,只有传授》 安德森:你关于丹尼埃尔·于伊耶与让-马里·斯特劳布夫妇的这部电影(《何处安放你藏起的笑容?》)常常被描述为一出浪漫喜剧,有点接近斯坦利·卡维尔所说的“复婚喜剧”(a comedy of remarriage)。它有时被拿来和霍克斯的电影作比。另一次,你则提到了刘别谦的《回转姻缘》(The Marriage Circle, 1924)。你想谈谈这部电影的喜剧面向吗? 科斯塔:这样开头好难。 安德森:你要换个切入口吗? 科斯塔:这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我们之间私人的关系。让-马里真的是我的导师,我完全能理解他在对我讲述什么。我知道这里有些不应该讲出来的秘密,最好保持私隐、保持隐秘。但在这部电影里,让-马里已经这样做了:呈现自己、暴露自己、展示自己的爱情故事,正如展现他的知识、感性或者感知一样。他描述与丹尼埃尔初次相会的方式,是他为我、为你做了什么的最好例证,当然也是在这间小屋极大的张力与极大的(可以说是)煎熬——但他们不会喜欢这样的词——在紧张工作中做了些什么的最好例证。他如此勇敢地这样做了,讲出了他们爱情故事美妙的片章,个人的、私人的片章。而他本不需要说这些的,可以只谈谈《西西里岛》(Sicillia!, 1999)的剪辑、电影、观念,和学生们分享点什么。 这样的活儿是他们眼下找到的得以拍摄电影的法子,或者该说是别人给他们找的。继续创作对他们来说真的非常难。他们有句名言是,“这将是最后一部电影”。他们总这样说,而这完全是真的。不仅因为他们把每一部电影当最后一部来拍,更致命的是,筹钱并且把片子完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比如就我所知——因为我最近在他们的一部电影里帮了点忙——给他们工作的人几乎不要钱。当然,其中有很多乐趣。我可以告诉你,我拍他的这部电影,花了和《西西里岛》一样多的钱。这是为什么他们采用了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到法国这个学校来完成影片,他们来这儿讲讲剪辑、电影、讲讲你能看到的这些内容,作为交换他们就能在这儿剪片子,并且能拿走一个拷贝。只有一个。我想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法子了。他们过去的四五部电影都是通过这样的研讨班完成的。 我从头到尾都在那儿。正如你所看到的,拍摄是顺序进行的。他们在第一个场景开始,在最后一个场景结束。历时一个半月。有些讽刺和预示意味的是,第一天这儿还有三十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一女两男。这很令人伤感,简直就像他们电影的放映一样,人们纷纷退场。 安德森:只是有时候。 科斯塔:只是有时候。不过留下的人还在。我也有拍到他们在那间学校的电影院里放电影。我留下了两三个关于展示的镜头,很简单就是为了这个电视系列片《我们时代的电影》(Cinéma, de notre temps)那带点说教的意图。它的初衷是要让你知道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到底在创作什么样的电影,所以理应有说教的面向。但对于让-马里和丹尼埃尔来说,这更为复杂深入。对他们来说电影不是孤立封闭的:它必须有态度,它关系到日常举止。所以其中包含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存在方式。片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美丽的瞬间,是让-马里放映《恩培多克勒之死》(the Death of Empedocles, 1987),他谈及理念与梦想,这个梦想或多或少和他正谈论的那个人——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是相通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其中也有些他与丹尼埃尔穷尽一生在电影与生活中追寻的东西。他可能是世上以生命与艺术将这份梦想耕耘至深的人。我必须留下这一段。这段的最后,他对自己的艺术人生做了概括,对观众说,“我们开始了,很难,但我们乐在其中,将继续向前。”我清楚我必须将这些时刻留在影片中,否则它将是不完整的。 在此我也想否决某些关于斯特劳布的共识或者标签,那些说他们是智性的、艰涩的、与世隔绝或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恐怖分子或者其他什么的。在我还小的时候,你绝不会去看这种人拍的电影的,即使他们是你的朋友比如《电影手册》的人。我从来不同意,实际上他们也不同意——我们聊过——这些规矩和口号。这就像在说:别去看这些电影。标签制造了漠视。它就像在否定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自然感知,自由观看与欣赏的能力。我们本该是无拘无束的。但当这些文化标签出现,漠视也随之而生。我觉得这非常野蛮。它们没有阻止我去看(斯特拉布夫妇的)电影,但我知道它们唬住了不少人。有的人可能去看了,但不喜欢,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方面。好像你必须要知道银幕上是荷尔德林、卡夫卡或者勋伯格你才能喜欢斯特劳布。不是这样的。你就去就好了,你会听到,会看到。如果你喜欢,你可能会随之发现勋伯格或者帕韦泽。这种语境里的“文化”对他们(斯特劳布夫妇)来说毫无意义。就像丹尼埃尔所说的:这是关于给出或者接近某种东西的努力。人们因此有所获。这也是我接下这个电影的原因。也是为了抗议那些毫无贡献的影评人,他们主要来自法国、美国。我不是说他们糟糕至极,但他们毫无贡献。所以我也想让它有点轻喜剧的感觉。 安德森:你还说过,对你而言,最好的电影同时也是最悲伤的电影。而这部电影的结尾……我不知道,“悲伤”是否合适,但那确实是酸楚的。他们在一场放映的结尾,走进了影院…… 科斯塔:这部电影简直是每个电影人难以企及的梦,一个有意义还能大团圆的爱情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拍美满的结尾。我一直是把那当作美满结尾的。他很疲倦,而正如他所说的,这儿有贝多芬的音乐召回一点生机,可能是一刻的生机。他还有打火机,你看到了,而且你知道丹尼埃尔就在他后面,在楼上的什么地方。所以这很像刘别谦。这几乎是一场梦幻。怎么可能拍出像刘别谦的东西呢?我做到了一次。它已经结束了。我要继续拍悲伤的电影了。但我不觉得这是悲伤的。 安德森:对我来说,当你站在或者坐在你自己影片的放映厅外时,你总会感到有种特殊的孤独,因为你与那部电影的关系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你无法分享给厅内观众体验的方式。即使人们喜欢那部影片,我也仍然会感到孤立隔绝,对我来说,就挺悲伤地。 科斯塔:别这样。 安德森:好吧。 科斯塔:是会悲伤。对于竭力探索的人总是这样。拍这部电影特别好的感受是,一切都在验证我曾经的期望。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但都来自电影节之类的渠道。下决心拍它对我也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已经筹划了好几年了。曾有三个人试着做都失败了。是(制作人)杰妮·巴赞(Janine Bazin)与安德烈·拉巴特(André Labarthe)向我提议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斯特劳布夫妇的影迷,总在采访里提到他们。当他们问我是否有意加入时,我说,“我得想想,这有点吓人。”不是说他俩,我想我们能处得来。但该做什么呢?怎么拍呢?太难了。说来话长。我去罗马拜访了他们,我不知道应该和他们说什么,于是我和让-马里在酒吧中沉默了一个小时。度过一个小时后,他问我,“所以这部电影怎么办?”我说,“我觉得我能拍。”他又问,“那怎么做呢?”我说,“我想拍你在法国剪辑的过程。”然后,我记得他这么说,“那不可能,你没法拍到,视听转化不了。”而我说,“或许吧。”但我在另一部电影里有过这样的经验。拍摄《旺妲的房间》(Vanda’s room, 2000)时,有时在她的房间里,我得到了这样的感觉,我置身房间中,事情开始变得不同,墙壁仿佛在移动,旺妲在说话,时间与空间在我面前展开。我对一切了如指掌,远甚于寻常的拍摄,我非常非常确定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他(斯特劳布)说,他答到,“我保留意见,但如果你不会打扰到丹尼埃尔的话,我们就试试吧。” 他跟我讲了个很有趣的事。他说,“但别忘了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什么艺术秘密,我们毫无隐藏。”我想这是之前的计划出问题的原因,他们想找出这些疯狂艺术家是怎么做事的。因此,选择拍摄剪辑过程是我对此的答复,接近于不存在的秘密,只是拍摄工作本身。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正如丹尼埃尔说的,这关乎信任。一点一点地,我想他们看到了我和负责录音的马修·因贝特(Matthieu Imbert)在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工作。当然,事情都清晰了起来。我所思及、预测的成了真。非常幸运,我见到了、认识了从小就喜欢、幻想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好像喜欢他们这件事在我的因果之中。有非常诗意的缘由。我是对的!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知道自己是对的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创作,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人生也是。他们是如此的配合、慷慨,正如你能看到的,他们一直在那儿。 安德森:影片或许没有透露什么秘密,但它传授了很多东西,不是吗?关于耐性、专注、削减,关于形式从何而来、如何做出剪辑决定。我想这对于那些感兴趣你如何拍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影片,即使你不百分百同意他们说的话或者他们的方法。我时常想到他们的理念,有时显得过于专僻和深奥,但其实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类型的电影创作中。 我可以从我的经历里举个例子(安德森曾经在《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 1984)里出演了个小角色)。他们电影中的表演以好莱坞标准看是非常奇怪的,可以说是布莱希特式的。其中的表演方式确实是对布莱希特的援引。这意味着,演员要给出真相——他们是在引述。我记得1983年拍《阶级关系》时,有这么一场,丹尼埃尔对我们说:“别想着表演,除非台词已融入你血液之中。”我觉得所有演员都应该遵循这条规则。这将杜绝许多差的表演。但实际上演员大多在还不了解台词的情况下就开始表演了,他们由此养成了坏的习惯,在说台词时不断重复自己。 观众:我想问问汤姆和斯特劳布夫妇一起工作时的经验。他们(一个镜头)拍了多少次? 安德森:二十次。 观众:次与次之间他们如何指导? 安德森:丹尼埃尔会说:“眼神别偷懒。”我就记得这个了。在你(科斯塔)的影片里,他们讲到了克里斯蒂安·海利驰(Christian Heinisch),《阶级关系》的主演。那个男孩非常聪明,就这部电影他们一起工作了挺长时间,大概三个月,他很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有说过,他是共事过的演员中唯一一个知道该如何看的吗? 还有和佩德罗所说有些相关的另一件事。《阶级关系》对他们来说算是大制作了,拍摄时间很长,大约三个月。大部分拍摄在汉堡进行,但最后他们去了一趟美国,带着两三个演员和其他剧组成员。组里大概只有六七个人。两个录音,一个执行制片,摄影和助理,可能还有两个灯光。 全片用了25万美元,35毫米黑白胶片拍摄。每个镜头都拍20到30遍。所以他们也说,“你看,某种层面上,我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电影人。”通过简化制作的其他方面,他们找到了一种能让自己做所有该做的事、需要拍多少遍就拍多少遍的方式。这中间差别很大:当你有个六人的组,你是个导演,当你有一百人的组,一堆场务车之类的东西,你就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了,你得做一个指挥军队的将军,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说有多些邪恶,但差别很大。组小的时候像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人人去同一家餐厅吃饭,住在同一间宾馆,晚餐后一起在宾馆酒吧喝酒。唔,丹尼埃尔和让-马里不去喝酒,他们得剪片子。 我还能说什么呢?噢还有件小事,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那是令我印象很深的。我进组进得比自己的戏更早一些,旁观他们拍了一段时间。他们和演员、组员在有一个景拍了白天的戏,拍完大家都走了,只剩他们留下来清扫:他们真的跪下来擦地板,把场地还原成拍摄之前的样子。当大家都去吃晚餐时,他们留下来做了在所有其他剧组里都是剧组最底层职员该做的事。 科斯塔:让-马里曾跟我说过,他作为导演主要是在捡烟头而不是指挥演员。 观众:你谈到拍摄这部影片某种层面上是对一些影评的回应,包括法国的和美国的。我不了解这部分内容,你可以讲讲是什么样的影评吗? 科斯塔:可以去图书馆找。 安德森:如果你会法语的话。 科斯塔: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阵子对影迷产生影响的两股力量是戈达尔和斯特劳布。作用力很强。对我来说,斯特劳布远更亲近。到现在也是。他们与我对感知、暴力、柔情的信仰更为接近。可能因为其中有些更残忍和生鲜的东西,不带伪装的。这是斯特劳布令我喜爱的地方。我从斯特劳布得到了共振,而戈达尔没有。在我看了所有斯特劳布作品之后,我突然觉得戈达尔非常老旧。而斯特劳布是最快、最激烈、最美丽、感性、古典又摩登的。对我来说这毋庸置疑,但要说服别人不是件易事。 所以我读了这些毫无贡献的书。有的还不错,但还是得说关于斯特劳布的讨论大多……没有很好地谈及电影里的感知原理。而这时我在这部电影中想要铭刻的,我自年轻时就感到的东西。斯特劳布夫妇常常这样说,“我们的电影里并非没有心理。”他们说,你如果好好看的话,你能看到些什么的。他们从来不避讳“情感”、“张力”这样的词。你在这部电影里也可以看到电影是如何运动的,在那个剪辑室里,我们始终在追逐这种张力,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你做这样的创作,这种张力也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张力是令人难熬的。如果能够每天、每时、每刻都与之共处或许也不错,但那不可能。他们或许已经是……已经是在这一点上程度最甚的人了。这儿的“张力”,(tension)可以换成“激烈”,不过还是张力吧,一种紧绷的感性,对万事万物之存在的感受,就像在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的细节一样。要先看到这些东西,你必须一百分地投入其中。你没办法保持每天都这样,那会让人精疲力尽的。但每个人都应该尽力如此生活。我想,这就是他们所传授的。每个人都应该像巴赫作品一样绷着,不是“复杂”、“艰涩”,而是绷着,这更加简单。 观众:人们总是说斯特劳布而不是于伊耶,是因为他是更占主导位置的创作者吗?他有参与过与戈达尔的论辩吗? 科斯塔:那些文章是别人写的,在新闻、杂志或者期刊上。有时他们会说“马克思主义”“毛主义”“恐怖主义”“形式主义”“爱因斯坦”“福特主义”,什么都有、互相矛盾。我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它们蒙蔽像你一样不了解斯特劳布夫妇的人。所以让我们先看电影,再读写关于斯特劳布的好的文章——我可以分享一些,然后你可能会忘了这些标签。 安德森:或者我们可以说有时候它们的电影已经不是智力讨论的关注点了。影片只是理论化的对象,而理论化本身也不够好。她还提到一个问题:他们是合作者,但为什么人们总说让-马里而不提丹尼埃尔? 科斯塔:我想你对此和我一样清楚。首先是因为他是男人,电影人好像总是男人。另外我想也是因为她喜欢这样的位置。让-马里是很爱表现的。可以说他是个逗哏的人。换年轻时候,他可能像是法国北部的詹姆斯·迪恩,天资聪颖……丹尼埃尔说,你对别人可能是天才,你在家简直是灾难。看得出来,他就是个大男孩,而丹尼埃尔扮演着女性的角色:看顾他。他们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一起剪辑,不过在前两部作品里,演职员表写的是“让-马里·斯特劳布执导”,而丹尼埃尔挂的是剪辑,或者制片。后来变成了“由让-马里·斯特劳布与丹尼埃尔·于伊耶执导”,而现在,则是“一部丹尼埃尔·于伊耶与让-马里·斯特劳布的电影”(A film by Danièle Huillet and Jean-Marie Straub)。 安德森:我想还有个原因是,听他们说话或者读他们采访的时候会发现,常常是让-马里滔滔不绝二十分钟,丹尼埃尔用一句话总结。他说很多,但某种层面上,她有更多可以说。她会鞭辟入里直指他花了超过二十分钟试图传达的内容。你们从已经发表的那些采访里可以看出来。 科斯塔:她还总是纠正他的小错误。斯特劳布说1914年,她就纠正:“是24年”或者“不是他们,是他们”之类的。但现场工作又会看到让-马里的另一面。他更焦虑,总躲在摄影机后面,而她扮演艺术指导的角色,也和演员站在一起。 安德森:在我经验里,现场是让-马里控制影像而丹尼埃尔指导演员、掌握声音。 科斯塔:她也管服装、道具等一切别的事。我想他们电影中有很美的一部分来自于她——那种富有韵律的狂怒,她是如此克制。就像《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aron, 1975):她是让-马里的口。在剪辑过程中她有紧张感,但她实际是冷静、克制的。也会紧张,但比让-马里更克制。让-马里有时高度敏感、非常忧郁。而她要做的就是把他从阴影里拽出来说,“闭嘴”,他总是有很多废话,而她会说:“杜绝废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闭嘴”。他们共同工作,以搭档的方式,我想那从不偏重于某一方。因为他们如此相爱。 *对话结束11天后,丹尼埃尔·于伊耶于2005年10月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