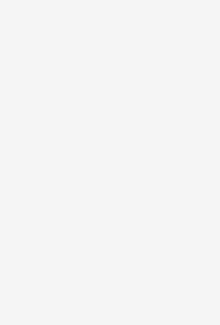孩子王 更新HD国语
分类:剧情片 剧情,剧情片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87
主演:谢园
导演:陈凯歌
更新:2023-12-28 17:04
简介:文化大革命期间,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谢园饰)被抽到云贵山区..文化大革命期间,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谢园饰)被抽到云贵山区的某简陋小学担任老师,知青伙伴高兴地称他为“孩子王”。但那里师资奇缺,教材稀少,学校分配他教初三,令他吃惊不小。老杆苦恼于学校的政治学习材料多如牛毛,批判文章学了一篇又一篇,但孩子们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不认得,老杆感慨万端,只得从头教起。 节选自戴锦华的《断桥:子一代的艺术》一文(《雾中风景》和《昨日之岛》中均有收录)。关于“父子秩序”的论述,请参阅原文。 在《孩子王》中,陈凯歌将直面这悖论与窘境。他终于以一个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流浪、孤独的理性沉思者的自觉讲述了他(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红土地的故事,一个知青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第五代“赤膊登场”。这是“第五代的人的证明”[1](郑洞天)。然而,即使在《孩子王》中,“文革”仍呈现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影片中的主人公与其说是知青老杆,不如说是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影片中的被述事件与其说是一个知青在“文革”中的一段平淡而有趣的经历,不如说是第五代对其创作的历史窘境的自指与自陈。影片中知青老杆短暂的教书生涯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能指,它的所指是历史与语言、语言与非语言、表达与不可表达之物。这是一部真正的自我指涉的影片。影片中四次用固定机位正面拍摄嵌在画框中的画框——门窗中的老杆(陈凯歌),来标示影片的自指性质。如果说,在《一个和八个》中,叙事人占据在王金的位置上表述了第五代们来自于双方相向的创伤性震惊体验——一侧是日本鬼子离去后遭焚毁的村庄,老少妇孺尸身横陈的屠场,来自于人类的兽行与暴行的震惊;一侧则是大写的他者/主体/群体的无端而权威的指控:“你还好意思看着?!都是你们帮着鬼子干的!”他(他们)竟要为这暴行承担罪责。那么在《孩子王》中,对老杆的困扰与潜抑同样来自相向的双方:一边是竹屋教室的隔壁传来的清晰、高亢的宣读课文(关于“老工人上讲台”)的女声,那是政治/权力/历史的话语,那是语言的存在与表达方式;一边则是蓝天红土之上不绝于耳的清脆的牛铃声与白衣小牧童呼啸着跳跃而去;那是一种非语言之物,是真实或曰历史无意识的负荷者,那是无法表达、也拒绝被表达的存在。同样的主题动机将再次出现并加强:在一个灯下老嵌在窗口中的特写镜头之后,切换为夜空中一轮明月(永恒、无语的自然、非语言之物的指称),同时画外杂沓的人声涌入,那是用各种人声、方言诵颂的“百家姓”与“九九表”,混合着庙寺的钟鼓、山民的野唱[2],镜头切换灯下老翻动字典(语言之源、象征秩序的指称)的双手特写,混响在加强,夹杂着艰难的呼吸声。那是一个语言的空间,那是一个被语言、历史的语言充塞的空间,那是历史的压抑力与阉割力显影的时刻。蓦然,混响终止了,一片宁静,画面切为老杆持灯走过,向右走出画框。在画外吱呀开门声后,我们在一个近景中、在与举起油灯的手同时升起的摄影机面前看到了老漠然而疲惫的面容。反打,门前一头小牛美丽的身影。小牛向左跑出画框。这是在语言、历史的话语与永恒的、无语存在之间挤压得无法呼吸的老杆(陈凯歌)。第五代及整个1980年代中国文化反思热的真正动机在于揭示中国父子相继、历史循环的悲剧的深层结构,并且探寻结束循环、裂解这一深层结构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历史的存在与延续远不是孩子王(陈凯歌)们所可能触动或改变的。影片以一具并不硕大的石碾隐喻着这历史的存在,老杆曾数次与之角力,试图转动它;但除却木轴发出阵阵挣扎般的尖叫外,石碾岿然不动。当老杆最终离去(被逐出)的时候,他只能以一种自谑与游戏的姿态踏上石碾并滑落下去。但老杆们的悲剧不在于他们无法触动历史自身,而在于他们甚至无法改变历史的话语/父亲的、关于“父亲”的话语。他们结束循环的渴望首先会碰碎在历史话语的循环表达之上:“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 老杆(陈凯歌)们深知:历史真实/深层结构/无意识并不在他们一边,并不在课文(关于“亿万人民、亿万红心”超验之父的权力话语;关于“平静中的不平静”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历史真实存在于绵延、沉寂、万古岿然的红土地(在《孩子王》中,陈凯歌曾两次以逐格拍摄来呈现从黎明到黄昏的红土地)、黄土地之中,存在于王福之父——王七桶一边,存在于清越的牛铃、吱呀的石碾树墩的年轮之中。白衣小牧童就是这无语之真实的一个隐喻性指称。于是在《孩子王》中,第五代的自指是自我尊崇的,又是自我厌弃的。他们要点亮灯火,去烛照洞悉这历史之真实/历史无意识——在老杆的视觉镜头中,他举着一盏油灯在教授,每个学生同样在一盏油灯下抄写,那是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自况;而在下一个真实场景中,老杆举着油灯,迷茫地注视着墙壁上自己的镜中之像,碎为两半的镜子映射出两个并不对称的老杆的影像;少顷,老杆自唾其镜像——这是一个破碎的镜像,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自我。一边是创造语言表达,揭示真实的使命感与渴望;另一边却是失语与无语的现实。在黄昏的暗红色的光照中,老杆曾与小牧童同在一个双人中景镜头之中。当老杆以教导者的身份要将语言/表达传授给他(“我认得字,我教你好吗”)的时候,小牧童却掉头不顾而去。小牧童的大特写视点镜头切换为全景中的老杆,摄影机缓缓地降下起伏的红土地渐次升起,将老杆隐没在沉默的土地背后。第五代们执着地注视着这土地、这历史。这真实的历史视野不仅将被土地所遮断,而且他们将被充满在中国天地间的历史的美杜莎式的目光凝视并吞没、掩埋在无语的循环之中。他们表达历史真实的努力,结果只是表达了他们自己,并最终为不可表达的历史真实所吞没。作为和老杆小牧童的一个等边对位的形象是文本中的“子”的形象王七桶之子王福。他顽强地要识字,要代父(无语的历史真实的负荷者、不可表达之物)立言:“父亲不能讲话。我要念好书,替父亲讲话。”但他唯一能做的却只是去重复,去抄字典,加入历史话语的循环之中。王福(他曾在同一的由正面固定机位拍摄的镜头中取代了老杆在画框中的画框的位置)与老杆再次构成了一种循环这是一次撕肝裂胆的绝望的循环:因为它竟存在于一种表达循环与超越循环的突围之中。 第五代的最辉煌的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以揭示老中国的历史之谜,并且最终消解历史循环的话语;结果只是老杆般创造了一个“牛+水(无法打出)”字,那是关于小牧童的一种真实境况的象形表述,却只是一次笔误,一个无人可识、不被认可的图像。老杆最后的话语:“王福,今后什么也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是写在屋中巨大的树墩之上。文字也如同匝密的年轮、暗深的龟裂一样,成了无语(非语)之真实的一种纹饰。他们终为象征秩序所拒斥,而终未能改变为“子”的地位。他们的艺术依然是“子代”的艺术,他们超越裂谷的努力只建造了一座断桥,一次朝向历史真实却永远无法到达的自我指涉的意象。影片的结尾,在小牧童的大特写镜头之后,是十八个镜头组成的扭曲的人形的树之残桩与老间切换的蒙太奇段落。在剪辑切为老杆的特写视点镜头之后,是一个烧坝的长镜头,滚滚的火焰与浓烟没过整个山梁。凤凰涅槃般地,陈凯歌再次寄希望于焚毁。焚毁将临,但它并不是以第五代所预期的形式。他们将再次遭受震惊。 …… 在《孩子王》中,陈凯歌以一种孤独漫步者的自觉,绝望地要通过拯救关于历史的表述以拯救自己,要从父亲话语充塞的空间拓出一方子一代的语言空间;于是他的表达成了关于表达的表达,他的预言成了对语言自身的期待;面对历史,对语言的期待变成了一场等待戈多式的挣扎。 --- [1] 郑洞天《从前有块红土地》,《当代电影》1988年第1期。 [2] 参见谢园(《孩子王》中老杆的扮演者)《他叫陈凯歌》,《当代电影》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