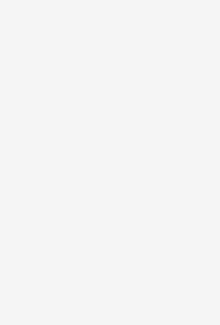海鸥 正片
分类:剧情片 地区:美国年份:2018
主演:伊丽莎白·莫斯,西尔莎·罗南,安妮特·贝宁,寇瑞·斯托尔
导演:迈克尔·迈耶
更新:2023-06-18 13:33
简介:故事发生在沙俄统治时期的一座俄国庄园内,妮娜(西尔莎·罗南..故事发生在沙俄统治时期的一座俄国庄园内,妮娜(西尔莎·罗南SaoirseRonan饰)是居住在那里的一位少女,天真而又单纯的她对爱情有着非常浪漫美好的憧憬,对未来的生活也抱有着极大的希冀。康斯坦丁(比利·霍尔BillyHowle饰)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同时也深深的爱着妮娜,对她进行着火热的追求。 康斯坦丁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伊莲娜(安妮特·贝宁AnnetteBening饰)带着一位名叫鲍里斯(寇瑞·斯托尔CoreyStoll饰)的作家前往庄园修养,在此期间,妮娜被放荡不羁的鲍里斯所吸引,然而鲍里斯实际上是一位浪荡的花花公子,他并不是真的爱上了妮娜,只不过是在玩弄她的感情。 第三幕里,索林的管家,退伍的陆军中尉沙姆拉耶夫准备好了马车,把苹果和梨满满地灌在衣服里,要给即将出发的大家带在路上吃。他对着观众说起记忆中看过的戏剧,其中的演员和表演,甚至记得出错的台词:我们中了奸鸡(奸计)了! 原文中本是轻松的桥段,一个不成功的冷笑话,巴图索夫的处理却更为沉重,他让管家大喊:我们中了奸鸡了!不仅是剧中剧里走样的台词,更像是质问:我们中了命运的奸计了?!沙姆拉耶夫总在高声嚎叫,叫声里都是对过去的调侃和念念不忘。他的生活里只有记忆,似乎靠记忆活着。从衣服里掉落的苹果和梨在舞台上四处滚动,又从舞台四面扔向他,攻击代替了祝福,他躺在地上,宛如一只束手就擒奄奄一息的海鸥。 沙姆拉耶夫这个小角色在巴图索夫的改编版本里变得重要,甚至出现在特里波列夫舞台背景的抽象画上,画里他正和一条狗守着粮仓。 巴图索夫大胆而极致的改编里充满了“偏不”的反其道而行之,让对话变成独白,用节奏和夸张肢体塑造出人物可笑的一面,每幕结尾都会现身和全体演员一起乱舞,在把舞台变成废墟之后起舞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幕。开头巧妙地提前了戏中戏,以特里波列夫的独白开始。最先破坏舞台的是乱入的巴图索夫,结尾处先把自己砰了的也是他,双重的痛苦和破坏力,就让梦想变成废墟吧。意外的是,特里波列夫的自杀如此悄无声息,告慰他的只有象征眼泪的玻璃珠落入脸盆的几声晶莹。 导演爱用的乱舞BGM:https://music.163.com/song?id=4090049 巴图索夫把原文本中带有伤感倾向的部分处理得轻松戏谑,渲染抒情的时刻则在意料之外出现。除了沙姆拉耶夫,还有突然跳上桌面热泪盈眶唱着香颂的医生,有最后妮娜语无伦次地说自己来到院子看到舞台还立着,两年内第一次哭了出来,这里说到舞台立着的她和特里波列夫相视一笑,眉头一蹙,又心酸又释然,也令人心碎,在多次重复铺垫之后抵达更安静的娓娓道来,丰富了原文本的层次,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变成两双手,他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第一幕中首次排练的台词。 巴图索夫偏爱不厌其烦的重复。重复争吵和重复表白,最后死亡之前的相遇,三次重复甚至不够,每多一次重复便更放大情感漩涡。重复并非复制,对话渐渐破碎,甚至不限制演员,大家轮流重现错乱,轮流死亡,全员皆海鸥。不停地死去,正如逃不开的命运。 死过一次的特里波列夫最后还是选择去死,哪怕他终于和妮娜重聚,发现她即使过得很不好,仍有勇气应对充满苦难的生活。在他搭起的舞台背景抽象画里,乌云旁边的太阳下写着“妮娜”。她是驱散阴霾的太阳啊,他甚至曾经跪着用笔纸描画出她的脚印的太阳啊,他曾坚信表现生活“不应该照着生活的样子,也不该照着你觉得它应该怎样的样子,而应当照着它在我们梦想中的样子…”,如今他发现一直向往的太阳暗淡了,妮娜的脸上只有硕大的黑眼圈和两行浊泪。想到王菲的《阳宝》:无论我多想是个太阳,却只是另一株向日葵。而月亮在舞台上以拴在秋千上的白色塑料袋来呈现,形似也意似,月亮像塑料… “一个像你一样的年轻女孩住在湖畔,她像海鸥一样喜爱这片湖泊,像海鸥一样快乐自由。有一天一个人偶然走来,看见了它,因为无事可做,就毁灭了它”,这是第二幕里作家特里果林构思的短篇小说《海鸥》的题材啊,怎么就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呢?!剧中的这一段被全员轮流演绎了多次,每次都会有可怖的女人从门后冲出,她们代表着恐惧吗?是一只只海鸥吗?是构思里偶然走来的那个人吗?无论来的是谁,无论如何碰巧,都将迎来重复的噩梦结局。而妮娜最后说的那句“我像在做梦啊”,是啊,为什么没有这种可能?不是见到名人的美梦,而是无法逃离的噩梦。 巴图索夫似乎有意强化妮娜和玛莎,特里果林和特里波列夫间的同步对位。妮娜开始中意作家的第二幕,在现场完成了变装,她头上的花儿消失了,她的外衣从白色变成黑色,她从海鸥变成别的什么类似阿尔卡基娜的女演员。作家对她诉衷肠,恼于写作剥夺了自己的感受,一边说一边把满桌的鲜花和果子打翻,遍地狼藉中他崩溃了,摊在桌上,像一只海鸥。此时,舞台后方响起了枪声,特里波列夫的自杀和作家的崩溃是同步的。此时观众的眼泪可能已夺眶而出,下一秒又很可能被妮娜的古怪咧嘴表情逗笑。 第三幕的约会邀请,妮娜重复三次请求特里果林“给我两分钟”,从动心到坚定到卑微的不同版本,一层层露出更深的情绪和更真的现实,终于没有要到那两分钟。妮娜和玛莎干杯,感叹:多么无聊的人生啊...这是巴图索夫表露温情的时刻,他让她们在舞台上一起抱头痛哭。当第三幕最后妮娜在舞台左侧端坐着等到特里果林,看着他流下眼泪时,特里波列夫在另一边独自坐着,包着头,流着血,仿佛被她的爱意灼伤了,而作家在接受妮娜的邀约时没有任何喜悦。曾经,玛莎在舞台一侧拉住特里波列夫不让他离开,他却执意要走向另一侧的妮娜。 第四幕里,巴图索夫和特里波列夫重复讲着妮娜的近况,对话渐渐变成独白。索林附和说她曾经那么可爱,自己都要爱上她了。他们说笑着,调侃索林是个“唐璜”,对妮娜漠不关心。 依然感叹契诃夫无懈可击的台词,第一幕的开头:“——你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衣裳?——我给我的生活挂孝啊”,后来看了《红与黑》,怀疑玛莎是契诃夫从司汤达笔下接过来的人物,玛蒂尔德的转世。第二幕特里波列夫对妮娜说起她青睐的作家特里果林:“这位才是天才,他像哈姆雷特一样走路,这个太阳还没照在你的身上,你已经融化了… “,接着这个“太阳”说:“我有什么美好光明的呢”,他不正是哈姆雷特?妮娜则成了奥菲莉亚。第三幕开头的玛莎决定”把自己的爱连根拔起“,去和教员结婚,让作家签名不要写“赠给我最尊敬的”,只简单地写“送给孤苦伶仃的不太知道为什么生在这世界上的二十二岁的玛丽雅”。第四幕索林说想做的事情没做成(想结婚,想待在城里),不想做的事情自己倒来了(当上政府顾问),医生说:“一个人到了六十岁还表示对生活不满足,实在是丝毫不合情理”。但索林想活下去啊,医生作为一个无所谓的“饱汉”能明白吗…医生曾说如果可以享受到创作艺术的状态,他愿意付出一切,此时舞台上响起了幻想中的掌声和欢呼,他享受的是热闹的欢呼。 特里波列夫不也像哈姆雷特吗?一边极速吐槽他母亲的吝啬和愚钝,一边强烈地渴望着她的爱,甚至在第一幕像个小姑娘似的扔花占卜母亲对自己的情感。在第三幕换绷带的场景里,他无助地坐在一片苍白中,宛如绷带怪人。母亲说,你像带着头巾似的…你几乎全好了…他可太不好了好吗?当他说自己终于感受到母亲的爱,爱似乎并不存在,连一丝温情都没有。第四幕里的纸牌游戏,母亲阿尔卡基娜说这是她小时候和妈妈玩的游戏,刚开始很无聊,习惯了也还好。正如人生。儿子拒绝加入游戏,反而想出去走走。于是桌上的各位大手一挥 ,让硬币在桌面乱蹦,纷纷做出弹奏琴键的模样直到失控抽搐。 《海鸥》的静谧是表面的,宛如水面,巴图索夫的改编把水面搅浑掀翻,摁着观众的脖子让大家看看水下,平静之下的荒诞和癫狂,生活的水面之下布满了吼叫。巴图索夫不关心水面,因此没有在服装和舞台上试图靠近契诃夫的时代,不模仿不复制,而是去接近它和他们的精神和魂灵,去呈现,甚至呈现文字本身无法呈现的。谢谢巴图索夫。 尤为感慨的是,契诃夫在《海鸥》中的思索和疑问跨越了时代,文字,舞台…跨越一切抵达了每个观众和读者。他就像第四幕里的特里波列夫和妮娜一样紧紧握住了每个人的双手。谢谢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