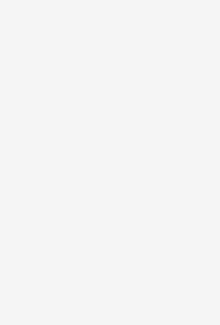你自己与你所有 HD中字
分类:纶里片 地区:年份:0
主演:内详
导演:内详
更新:2023-01-14 23:10
简介:影片讲述了由金柱赫饰演的画家英秀和他的恋人敏贞(李宥英)之..影片讲述了由金柱赫饰演的画家英秀和他的恋人敏贞(李宥英)之间的故事。英秀从别人口中听说敏贞曾和陌生男人一起喝酒,这件事引发了两人之间的争吵。英秀第二天去找敏贞,却发现敏贞、也有可能是和敏贞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也可能是双胞胎,也可能不是)在和许多陌生男人不停约会,而那些男人全部都是她之前曾经交往的男人…… 乍暖还寒的冬春之间,最适合看洪尚秀了。 为什么?有烧酒、做梦和性啊。 这些温暖又宜人的元素,反反复复出现在这个韩国导演的日记体影片中。 自成一国的视听语言并没有多大胆,也没有多新奇,男男加女女,故事被白描成不用解释的修辞。 被挑衅、被引诱、被说服,在那些林林种种的两人行、三人行中,我们就知道,日常有其正义性,没有谁比深情。 去年的中场休息,他被闹哄哄的绯闻灭了顶,但也似乎没有给旁观者过多的剧情,几乎活成了自己的电影。 男人都是真挚的流氓,没关系,这是爱情啊。 即使这样,他在访谈里说着,这些无用的时光,构成了一组画面。 那边沸沸腾腾的,每年一部的工坊出品还是要继续。 2016年推出的叫《你自己与你所有》,与他其他兴罗布阵的名字一样令人狐疑、尴尬与不知所措,你很难从中提取要义,这种孑然而止,欲说还休的谜题同样运用进他的故事里。 “完整的剧本是不存在的。”这是洪氏的创作法则,连带成为导演一职他也经常笑谈不是故意的。 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是故意的呢? 企图、野心、欲望,是这些东西构筑成为了“计划”,洪尚秀电影里的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他们原始的冲动会被直接,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场景,是只有“目的性”,而不具备“计划性”。 吃饭、喝酒、遇上旧情人或新欢、聊最近的电影、写一本日记,这些日常得像开水一样的事件为什么在洪尚秀的电影里反复出现却又有情有趣,很大的原因,它们都有点“离题”,没有上下文,喜欢偶发性,打散的日常因为重置的顺序而变得颇有意思。 《你自己与你所有》里,可以说是让这种偶发性发挥到最大。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认识你,你认识我吗?” … “我们在港出版社见过。” “我一次都没去过港出版社呀。” … 影片里通过不断的搭讪与拆卸,生出几段故事。 女主角敏贞与男主角英秀吵架后,就开始了类阿兹海默的健忘症,并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 记忆并不可靠,相遇即是正义。 随后出现的几位男演员,对于敏贞的失忆即使持有怀疑,但最终却乐于接受她的新面目,一切可以以新的姿态相识相知。 最荒诞的,莫过于最后,英秀在巷落发现敏贞,从执着的“捕获”转向了第一次的“相遇”,大家反而能好好相处下去,以一杯酒告别过去。 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真理被推翻后,一切都变得饶有意思。 电影中的相遇、分手,就像K的城堡,仿佛近在咫尺却又不得门而入(敏贞拿着的书正是卡夫卡)。 如果把这种“迷思”当作是洪尚秀的叙事技巧的话,人为的组装剧情,却并非按照推理的仪式开展,表面上看充满着荒诞未知的色彩,实际上是将生活的各种可能性铺陈开来,这当中,有浪漫的、狐疑的、残忍的,与未知的。 洪尚秀在访谈里提到, “我喜欢在重复的结构里观察,在这种结构里重建出新的东西。我希望有观众能在重复出现的场景和状况里有新的体会。如果你跟得上我的步伐、观察得足够仔细,在每一次重复里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细节,也许你没法解释,但每次的感受必定不同。” 《这时对,那时错》里简化了很多人物场景,从男导演与女艺术家之间的邂逅开始,将重心放在了两组剧情实验中,就像区间内颤动摇摆的叙事弧,毫厘之间,为什么这时对了那时错,导演一贯不做解释。 与之同时,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发生”的无意义性,一切的发生,并不存在强烈的因过来由,既无常又合理。 对洪尚秀饱含深情的文艺青年,一定都对剧中的人设颇有共鸣。 画家、导演、教授,男性拥有金钱和力量,是社会最基本的话语权利,如果没有呢?才华、学识,利用知识的不对等去引诱女性,同时其职业所带来的不稳定性、脆弱、甚至是神经质,反而激发了女性的母性保护欲,一切都变得可以原谅。而这样的伎俩,剧中人演得投入自然,而观众则看得满腹不平。 而看到自我的投影的文艺青年,突然顿悟了某种解决生活剧情的发现,那就是抛弃正常的对话逻辑,女人会更为你着迷。 尴尬并不可怕,它甚至就是一种美学。交流变得与对象无关,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情绪流动。 《你自己与你所有》里有有一段对话,是英秀去找敏贞时的幻想的,英秀作为男性,不断地用最直白的方式陈述着对敏贞的想念与爱意。 “我该怎么办,我真的爱你,敏贞。” “我真的很爱你,可是谁都不愿意帮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别的都不重要。” “我爱你,你是天使,只要有你就够了。” 他的重复,始终离不开我与你的关系,我是爱这个动词的赋力者。 英秀像一个孩子式的边说边哭,到最后,敏贞抱着英秀。英秀因为摔断了腿,只能坐着,但这种拥抱方式,更像母体亲近着残缺的孩童。 在这一次的《你自己与你所有》里,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承载出格、善变及纯真的主体从男性成为了女性,敏贞变得像游离的分子一样,随处遇见,又抓不牢。敏贞的出场方式是从别人的传闻中显现的,喜欢喝酒,醉了会闹,男女关系混乱不清。 但画家在为敏贞辩护时,却反反复复谈论了纯真一词。 纯真对于男人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些超乎常理的壮美事迹(sublime)必须通过“天真”的虔诚信仰才得以完成,因为理想化的天真在封闭的叙事中具有催眠功能:一方面在与理想化天真的对比下,可以使得故事中所有类型化的世俗伪善无所遁形。” (《电影.剧场和运动》) 所以我们迷恋纯真,同时又被纯真的残酷所伤透。 “你们都是可怜的男人。爱都是一样的,可是男人以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才会这样累。”英秀喝酒的朋友道出了一番话。 洪氏的尴尬美学由来已久,几乎每部片都会有所演习。 这种尴尬,无非来自于几种症状,不是被拆穿的伪善,就是赤裸的欲望。 这种断裂的上下文,缺乏逻辑的冲动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是尴尬,是因为我们极少有机会能够真正去面对它,更多时候,不擅长去处理一些“不成熟”的事故,这是我们尴尬的来源。 这种“事故”,是除了叙事及他生硬的推镜外,还由众多杂耍般的突兀细节拼搭而成。《不是任何人的海媛》里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或是《自由之丘》里多国语言的穿梭,制造一种意外的障碍,是他给予观众的尴尬。 醒来又睡去,谣言或巫语。 我们对梦的态度,多半是既期待又失落的,舔尝过梦的芬芳,全身都像涂了酥软的黄油,醒来却是黏黏腻腻的矛盾,深渊一样不可攻破的现实,梦之所以让人着迷且上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原始欲望的放肆与打击。 洪尚秀的电影里,不止一次利用了“梦”这个修辞,在他记实化的风格摄影下,他的梦不具备幻美的质感,倒是处处都是可疑的日常,这显然是种诡计,混淆了现实与梦之间的边界后,就像被针尖刺破的皮球一下漏气干瘪,全是满党当当的失望。 细数他过往的把戏,《不是任何人的海媛》中醒着梦着,尤为明显,全片都以海媛的梦穿梭前行;而《自由之丘》中缺失的某一页,永远也睡不醒的日本男子,靠着联想分辨真假。 《夜与日》中周旋在不同女人之间的小男人,被大梦惊醒,一只猪撞向了窗户,而你的生活还在滞留此地。 这一次的《你自己与你所有》,饶有趣味的是最后英秀跟敏贞复合后的一夜,睡前说着毫不真实的情话,睡醒后的英秀发现敏贞不在身边了,这让观众与之一起困惑起来,难道又是一个春梦吗?随后敏贞进入镜头,两人讨论起哈密瓜与西瓜,影片的结束就像镜头移出了生活之外。 观者与电影的机制本来就显得可疑,作为窥视的媒介,观众在使用、参与甚至进行自我解释时都无法躲避凝视带来的快感。欲望跟白日梦无异,他们不偏不倚地选择了你。 用性,来突破毫无生气的日子 我们谈及性的时候,会有一种大麻一样的刺激感。你要互相追逐,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捕猎的兴奋。 洪尚秀电影里的性,通常是家常便饭的存在,大家多是见怪不怪的,当然也无甚美感可言,多是情欲将至一蹴而就。 这种“限制级”某种程度也是在制造了一群尴尬脸,事实上,现实生活里的性同样唐突且迅速,一转眼你就被这投影抓住了尾巴。 人有本真和本性,这些直截了当的性爱场面,在叙事的维度里,又为人物突破着毫无生气的日子。 平凡的小镇掠影,无所事事的Loser人生,郁郁不得志的艺术青年,性爱宛如神圣之光,能够在那一刻扭转人类脸谱。 大家赤裸相见时,能谈的,也不过是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 搞艺术的男人,都是忧伤的嫖客。 在《你自己与你所有中》,关于性事的场面并不多,而尺度也完全在“关于”这件事上戛然而止了。 洪尚秀中性爱的场面针对的更多是性事前后人物的对话与行为,性事作为进入亲密关系最直接快捷的途径,既可以激发出被压抑的表演性质,也能撕开伪装的表象。 性的渊源如果取自于爱的欲望,理解这场欲望,并通过电影来理解的话,一切都简单得多了。欲望绝对是大于一加一的东西,不只是两个人情投意合的产物,包含了偏见、自我认可、目标以及冒险。 洪尚秀的欲望通常不是来自于视觉及感官刺激的,在大打折扣的真实里,我们看到那些真挚的流氓,全都乖张荒诞。 《处女心经》里,不断游说女人的男人,耍着性子的男人,甚至是最后执意要女人前来宾馆,都是为了简简单单的一句“因为我想。” 不加修饰的欲望,总是特别猖狂。 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家只知道一件事: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想要知道,因此他寻觅,他有欲望,他朝着它所没有但又能预感到的知识而行动。 这种寻觅没有任何保障,只是 ——- 正如柏拉图所言——-一种“美丽的冒险”(un beau risque)。(《欲望的眩晕》) 你们说爱情是魔力?那么恐怕都是因为有了性。 我们在讨论一种形式,一种手法,一种风格的时候,如果有着明显的个人创作痕迹,那么他的电影很容易就会归为作者电影之中。作者论的讨论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导演的角色,一个是导演的作品。 特吕弗(Truffaut)说,“没有好和坏的电影,只有好和坏的导演。” 我所看到的洪尚秀,与他的作品之间,慢慢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关系。 正是因为每年在重复结构里进行风格演进,除了他逐趋成型个人标签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观众。他们尝试找出这永恒旋律中的某些变奏,又为了这场回还反复的谎言寻找真理。 作者论把导演比喻成为电影的作者,摄影机就是墨水笔,这种主观创作意识固然重要,但与文学作品相比,电影始终不能脱离一种工业的产生,甚至也是一种商品类别。 但比起好莱坞的流水作业,摄影、编剧、演员,即便都缺一不可,但小工坊性质的确能让导演的自主权发挥得更大。 洪尚秀每年一部的小成本,几乎把艺术电影拍成了自己的类型片。“小成本”有时可能不是一种困局,反而是一种隔绝侵扰的界限,不用多,反而刚刚好。 比起《爱乐之城》在展演疯狂炫技的好莱坞工业,服化道美皆一流的世界舞台,洪尚秀的爱情奇谈反而更像一种变奏,使劲地将日常拧出了真相。 - Fin - 首发于“奇遇电影”下意识的人生,不需要必然的事件
空谈艺术,不如一起尴尬
梦里的自己,被自己伤害了
作者的电影,还是电影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