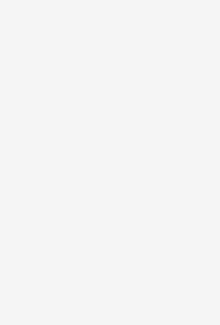粗日的怪谈 已完结 共6集
分类:日剧 剧情,悬疑,惊悚,恐怖,日本剧地区:日本年份:2020
主演:笠原桃奈
导演:山田雅史,鸟居康刚,平波亘,永江二朗
更新:2024-04-16 20:49
简介:由糸井繁里经营的网站“Hobo Nikkan Itoi S..由糸井繁里经营的网站“Hobo Nikkan Itoi Shimbun”上的热门系列“Hobonichi no Kaidan”已被改编成电视剧。 座鐘壞了。 每天到七點打鐘時候,原來是六點過半,慢慢地,這鐘兢兢業業朝前,原先該六點的光景,它開始發力,等到聽敲鐘,咣咣咣過去,最開始抬眼是六點半,后來是七點。它沒有秒針,但聽得見針響,默默前進,哪天一抬頭,鐘跑近八點,再往后,跑到了九點還沒停下。以往,它快到一小時零四十分卡吧一聲停住,手上弦子,恢復正常,但現在不,多轉三圈沒有停止跡象,林仁只好把它束之高閣,讓它一人悶悶地敲,另外買了個外形銀白的馬提鐘,放到座鐘的地方。馬提表左旁還是母親夏天在朋友家的寫字臺,微笑假裝在看報紙的相片。這樣使用近六十年的老鐘終于成為擺設。 但它一直敲。特別是晚上,林仁一人有時嫌小客廳沒暖器曠得慌,躲小間看書,冷不丁,咣咣咣——它就敲了,嚇林仁才想起這鐘,回頭看它那里已經深夜十二點。凌晨了……這么刻苦!林仁自嘲,回眼電腦邊角,表針剛過八點。林仁再看書,只不幾行就想回頭,瞅一眼倒添心口涼氣,里邊總像待著個人。這以后,在單位,林仁也暝暝間聽得見打鐘響。細微微、隱隱約約,那個時間,他常是陷在表格的趕寫或數次電話謝絕的時候。他家人曾戲說這屋里怕是有鬼,且此鬼有靈,不然鐘怎么在剛進小屋一段時間里走得特別準,大約過去三十天,鐘才想起加速奔跑。“像適應。它這也是適應”。林仁和家人不約而同想到后說出來。從這個月往后,它不斷地逼進,不遺余力奔奪,奪出些空間來,表盤上除了光潔的異樣外,沒發生任何該多出來里創造出的事。林仁只是想,鐘聽見那聲響的時候轉了整整一格,從4猛可跳5,打11直接擺到12上。是這樣的。他有時正看著黑格子填數據,忽地會想陰天時候,不怎么想往那邊看后說的這句。 同事楊有時問問題,發現林仁會忽然失神,叫一聲才回過眼前,并聲稱是因為頭疼,頭疼發作我好望周邊,不像其他人愛看遠處。其實這種時候,林仁是聽到那鐘咣咣咣……催促他。他有一段時間,曾想將鐘順五樓扔下。“就扔到那叢竹子,沒人發現,就解決了”,他沒對家人這樣說,所以每天他由這里走出小區,下意識躲蔽那個方向。因為沒幾年前,他親人的最后一個晚夏的鍛煉路也常往這而出。“那是片很美很深的竹子”,那里不會,不應該有個鐘從天而降,打破記憶。綠色的,潮潤的,竹子是次竹,細桿子一枝壓低一枝,有時攀上棵李子。泥土味,下雨后的泥氣,竹香,掩映著回憶。 林仁今年初夏,从市内迁进市郊,他在市内街道办的时候,担任行政,等到一百公里以后,领导让他去下边走走,每条街道上有多少老人,这些老人什么样子,前一天给那位老人打过电话后他有没有消失……诸如此类,是林仁按期匯報的工作。以前林仁常在屋內,現每天都得經過一條條馬路,他沒有車,這個街區的老人都住舊樓。 公交卸下后走小巷子竄門坊,林仁有時走著,忽地就失落,找錯樓棟、說錯話的事一多,等他走下一家拐進靜靜的小道,看見棵倏然而出的白杏花就站會兒,嘆口氣。林仁下访途中總在想,消失是什么意思,樣子又是什么。到后來,他走的白天孤伶伶街道一多,也就想通,消失就指死亡,樣子是你到那里以后對象的壯態。他一想死亡,馬上認為主任說的消失的確溫和,且是種關懷。但是他打電話過去的第二天,老人根本想不到要回啊?那你怎么準確斷定是死是活。同事小楊說慢慢地你就會了,林仁感到很窘,的確窘,這哪是該問的問題,本身自己就說出答案來。 林仁中午休息,跟窗格后同事聊天,說著說著就想到些很特別的老人。某位老人家里的擺設,那個寄居屋里的老太太,林仁走時囑咐不斷讓下次帶龜食的老頭,混入思緒,有天逼他談話間隙問出一句你們見過這么多奇怪可愛的人么?先是小楊笑勸,小林你這只是工作訪問,這是你的職責。重要的是讓你負責的街區一個孤寡老人不能往下走,往下走什么意思你是懂的。林仁看著小楊,再度感到自己還是幼稚了。 小林依舊在走,依舊走在一條另一條陌生的街道,拜訪一位接一位家居不同神態相似的老人。 直到有一天,紅磚墻里的老人出現,讓他后脊發冷以后,才想起那只鐘在他腦海里消失了這么久。 周六的一天,天氣晴和,小林選擇條遠道,先去表格上位置最低的一戶,因為他看到一個奇怪的名字。他以后想,正是這名字給他牽了條線,讓他很多年后都從這天不斷開始回憶。小林穿天藍短袖,藍色牛仔褲,肘彎擱著淡藍色文件夾,到那家紅磚門一米前的婆婆丁壇就停住了。他臉上滿了汗,用手背擦去,手剛離開額頭,就感覺出一種聲音。當時耳邊盡蟬,近八月末,蟬嗚改變,中間斷開,走道無人,顯得更為安靜。在那段霎時靜止的時間,小林感覺從紅墻里往外正透著什么,小林在紅磚墻面后,他看紅磚,縫子里敷著細茸苔子,底部潮濕的面積一大,許多塊磚赤中映黑,林仁摸了摸,一陣濕咸味道撲近,視線一躲,看到一個金屬邊的銘牌:寺忍。果然是日本人。他打開夾子,手捋著格子細看,寺忍這一欄,很安靜的一行字,上一年開始不久寺忍由日本的日暮里市搬到這里,家屬一欄是空。空著的……林仁不免看回字牌,墻頭顫出棵細瘦的枝條,上邊綻開小小白花,他眼前發昏,一會兒這種枝條變密,很多個花似乎在銘牌上下翻動,林仁視線更加模糊,再定神后很猝然地,余光邊有個更厚更圓的白色,他一挪過整只眼,發現這是個人。 她在紅磚墻里站著,就守在簡約的白漆鐵門邊,這一幕使得林仁,這個慣走老人住處的人,卻有一時發愣。林仁那個時候,心底總有種東西加過來,讓人感覺,面前這位老人的神秘是由他這邊過去的。早在他注目銘牌時,甚至在他停腳抹汗前她是穿過他走進來的。首先,她站著,穿件碎花間游引小蜂的灰褂,下襯鐵灰亞麻布折裙,她面朝林仁,眼光透過他,在他身后,冀著種愿望,對視一刻后嘴邊慢慢地圓上去。林仁被她獨特氣質打動,先就低低頭,像了鞠躬,她那邊輕輕地,很輕地低了頭,眼光被銀白發埋住,林仁見她半搭視線注視腳邊,那里是光光的水磨石地面,而沒多看一眼地磚旁茂盛的紫花地丁。 寺忍老人保留一切日本習俗,林仁都照舊做了,進門將脫下的鞋子公整地摞列。也許因為老人的肅穆,平常進來開門見山的林仁,開口前反特別留意第二層玻璃后的景致。這是扇花玻璃,高大揚天的鏤葉子芯,是朵朵打苞不開的花,花之上是近一米的空白,磨砂里林仁辨別出些影,像草在風里,也像含渾的小鳥,忽然地,霧黑黑地溜過幾個頭頂,那是墻外邊的孩子。白漆門細窄的鐵條柱檔不住,可能寺忍老人喜歡這樣。林仁回過臉,寺忍還微微笑著,看向他這邊。林仁突然感到很過意不去,連連致歉,話說完便后悔,寺忍她,能聽懂么? 寺忍不但能懂,后來的交談都是用中文,她的流利與相談間的從容,不能不讓林仁再次謹慎起自己,當問及些可能觸踫底線的事,都盡量緩慢、壓低,但寺忍老人像沒有在意,始終含笑的回答。寺忍老人起身給林仁倒茶,他才半跌著膝蓋,像個病人蹣跚起來,半撞著朝進門后首先注意的相片陣走。一共三張照片,沖著小客廳林仁的茶桌,相互間隔一扎安靜擺放。底座下邊的條桌,潔凈反光。纖細的塵埃、偶而掉片干枯花葉,這在林仁為他母親搭就的簡陋祭臺常發生的事都沒有。第一張是合影,祖孫三代,應該是祖孫,林仁隔沖洗水杯聲望老人側影,整齊有形,只不過那天她換了件夾的,他看飛翔小蜂,印象相似,轉過頭,相片中,照舊是穿梭其中,但是蝴蝶。展開膀子,忽閃忽閃,老人玉綠衣上隱約有樹枝,這些蝶飛。老人和詳,容長臉,長眼粗眉,右手來到膝外,牽上矮小的孫,身后父親形象拘緊,兩手稍一扶寺忍肩,鏡頭挪轉后就掉下來,反是那她手里的小孫,偎偎和和,既不依賴,隨處而安。 不要再看那個……了。林仁聽著這長音,察覺絲不幸,又不敢多問,但這恰恰是應該核實,眉頭緊了緊,吸口氣又覺得是否自己太敏感,耐心地回身去接遞近的茶杯子。 她和他又蜷膝坐回小桌。 你得多看這個,多漂亮,哎?我不很耽誤你……的工作?哎你?寺忍臉色倏忽萬變,這林仁都理解,先說了姓名。然后沒再細說因為寺忍國別而單獨來這一趟的時間寬裕度。 你還沒說有沒有影響啊?寺忍一面將下巴馬上抵住茶的熱氣,十分不安地探著顫動的頭,視線一直不離開林仁。 既然有這樣的碗,我可以多喝一杯,不礙事。 寺忍馬上笑了,換上安慰神情注視手中杯。等了半天,房間除了有屋外的夏蟬叫,一點聲音都沒有。林仁的眼光也就回到這杯子,下著霜,積厚變藍,迤迤萎萎,天際下降鳥的影子,但也像猜不清的字。這應該是山,寺忍猜出林仁想法沖口補充。不是霜么?過后林仁也就收笑,承認了老人的看法。再抬頭,寺忍改了神色,冷峻、孤凝,將對目光朝照片方向投了段柱子,這柱不是堅強,更不悲催,林仁琢磨著忘記剛才還有兩張沒有看。 是山, 那是我孫子。她用了種辯解的口氣說,眼神沒回過。林仁身上微微發冷,就放下了杯子。怎么?茶不合口?寺忍頭就轉過來了,窘措的林仁不好意思看她和藹目光。沒沒有啊。你不用像填表格一樣,那樣古板。古板到頭其實沒有什么用處。林仁涌上笑容,就相信了自己的記憶,將沙發邊打進門起斜靠身的藍夾子平放下,端了杯,也看向寺忍注視的方向了。 第二張那個單獨站的也是我孫子。他六歲,隨媽媽搬進個不大但溫馨的樓,六樓。我兒子哦,就是他,我那時候偷在心里怨,他總忙自個的事。期間寺忍打來的目光,林仁接過幾回,讓他心頭忽冷忽熱。他說他一定等拿到第三個獎杯再回到我這來,這應該……應該就是這周六的事。寺忍往上盯眼月份牌子,我這回說的是我孫子。她倒沒回頭,林仁只好打量她后腦勺,見了幾叢胎毛軟發,再斜頭看那個澀羞笑著的孩童。 屋子沉默了。林仁試到牛仔右褲小腿部位,踫了下,眼睛一恍錯,外邊一棵月桂掉下片大葉子,他打量房子四邊,才發現都是一種模糊玻璃,沒掉落的樹葉昏然在動,混混沌沌,霧篷篷,讓人懷疑剛才有東西墜下。叮……——!林仁耳朵刺痛,杯中水茶噴到木板上一灘,他顧不得,順聲循跡,哦原先進來并沒發覺,就在鞋柜左沖半個玄關,高出個幾子,一種鋒利的金屬刀片聲在劃振動的話筒。叮……!叮……! 那里有個電話。 他看寺忍。寺忍握住熱杯子看窗。他腳踩淺水洼有段時間,試出來,退回去,先放到桌上杯子,低頭擦地板水,眼光一高一沉,余光試著寺忍轉過視線,驚訝不已,那個鈴聲已消失。 怪我,是不是剛才忘添水了,我去把布找來,等會。寺忍根本不等林仁忙不迭致歉,抽身趕回廚房。林仁邊看她,頭扭著手里盡水,濕濕的,他不知道,不停擦水。 寺忍與林仁端起二開的茶水,地上整潔如鏡。引的林仁往下看,木紋地反光,透了水臘勁上來,映照寺忍寬身,此刻她又看向照片,林仁想到她說這周六孫子要回來,就抬頭問寺忍老人兒子一家經常見么,剛才說的孫子獲的獎是什么,這些寺忍老人都照著相片答,但沒具體指向,她只說一句,重復了三次,兒子和孫子這周六就能回來。 這天林仁大約十一點走出那個白漆門,剛邁進地邊有淡白雛菊的小石道,他聽身后寺忍說讓他下回再見的時間是不是要很久。他回過頭,只見到了寺忍老人的背影,也就沒再回答。 第二次見寺忍,領導特許林一整天的時間,希望他回來后將近況寫全。林仁實際想寫的東西上司看了也不信,走這一路就默念,盡量將看到的事記住,將來寫到能寫的紙面上。這次寺忍開門前擔擱了,林仁摁了又摁,心底開始害怕,門開啟了,寺忍剛起床,花白盤發掉落一柳子,一照面,懨懨表情收住了,接著門縫開得大了,林仁點了頭,一路讓著后邊慢走的寺忍,她淺低頭微微笑著,跟了進來。 這次見面氣氛融洽許多,他們能說起手不管用致使杯子撲地的笑話,寺忍笑得合不攏嘴,后來竟非倒臥沙發才略止住,過后她就指窗檐,讓林仁看小院也還有環墻白薔薇,說晚上等有機會你再來,這里有星星。林仁也笑,欣慰地光喝茶,寺忍雖說著,眼睛一直照顧茶杯水,剩下一半時她就站起來到廚房拿壺。林仁問寺忍什么時候開始喜歡種薇子,寺忍看窗外,又笑說……林仁恍惚間看到一年,他家里老人偷采黑柵欄里粉薔薇的身影,似聽非聽瞇著眼笑。寺忍介紹了許多花,她說她還有愿望,如果不死,打算讓這屋里七扇大窗,片片見臘梅。 臘梅!,臘梅可不是容易的事。林仁心頭被刺了下。一棵、二棵,合抱的龍爪樹參天而立,疏密間離的倒花鐘,固緊枯干,從天而降的冷沁,他躲枝和枝的洞,喊母親。臘梅偏熱火,寺忍的巨大聲音進來,林仁聽到,是冬天的爐子,我讓它爭取可弄到春暮,這是大活兒,你可以也來,你喜不喜臘梅?寺忍看窗說梅,聽梅,說菠蘿,說海棠,說有年土的顏色,說那種小時候怕的事,說到現在找不到一根雜草了,林仁感覺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 林仁準備站起來松松腿,寺忍老人倒頭認了認又回頭,嘴邊停住了,眼睛又落到照片中間那張。林仁一眼瞧見相框邊豎立的藥瓶,熟悉的黃箶蘆,就走過去,他指尖踫到外殼雕花時,電話鈴響了。他等待了二回合,屋子很安靜,他壓氣回頭注意寺忍,寺忍罕見地對視,和緩從容的面相讓林仁感到恐怖:您怎么不接電話…… 寺忍眉峰抽動了動,窗外下雨了,春蠶咬著葉子沙沙沙沙,她猛地解救般舒了眉看窗,哦,你先看見了?林仁瞳仁轉的很靜,跟上寺忍,她后身影子單薄、平穩。窗外,雨從剛剛落葉,到現在已經打濕桂樹直干,所有的綠葉子耷拉,霧塵、樹氣暈暈,寺忍的灰點子和桂綠塊子磨合,他認為這是夢。當灰點子終于正過來,變圓,他不想問那個問題。她倒解釋似地繼續說,我看你來時沒帶傘,夏天,哎這夏天…… 寺忍站起來了,他眼睛里只盯著她,窗外雨聲漸小,他一路跟她來到廚房,放上大理石臺桌杯子,聽到瓷杯底踫石頭的脆響,手抖著走近瀝水池子,掏弄了弄下水口,轉身過來摸杯子,嘩啦一下倒掉剩茶水,轉頭看看廚柜,扭頭就走,來到門口又回去打開了柜門,把杯放地上,向后摸夠時候側著頭,看見林仁,笑了,就是它就在這。拿出把紅傘,她輕輕往這邊走,林仁臉上訕訕地,不知道說什么好。她放到他沙發一落,那只枯瘦手慢慢伸過來,想拿林仁杯子,他一出手攔,我給你添點,再……寺忍顯得錯愕,一臉想問林仁出什么事的表情。 那個電話是真的?他試探著看寺忍,要是個玩具的話,那就……電話?我家里沒有電話。寺忍皺皴起的眉像是冷漠,林仁一看見再說不出什么,點了點頭。 林仁這次沒讓寺忍站雨后門前目送。他剛走出街口,雨立刻大起來,他在傘下抱緊胳膊,想這一天那間屋子里的人。窗外月桂葉子滴雨時候,他好像聽見鈴聲在響,他看著寺忍看窗,隱約間也聽見了鈴,前后間隔著,一波振一波,鈴聲消失在寺忍找出紅傘,她手一著上傘,鈴就像上次,突然滅了。他注意傘邊緣,掉下一注一注雨顆子,淺絳傘面映出上燈樓宇,林仁一驚奇,透過傘望望天,過去的時間……傘鏡里走過一桿電子屏,顯示剛不過三個鐘頭。我在寺忍家待了這么久。水滴結了個勻長的凸鏡面,寺忍正招手站在雛菊后邊門框上,林仁嚇地掉頭看了,除了平整的草地上一片水霧外,遠處的燈桿先亮了。這里離寺忍家已經過了那個滿是木香藤的廣場。 林仁回到辦公室,查起老年癡呆癥的資料,期間包括領導在內總共從他身后過去七八個人,都沒打擾他。傍晚向領導匯報,他沒說這段詭異的時間,領導說給他讓他多從老人方面設想,林仁感到不解,資料上關于老人近況已經概無遺漏。他想問清要求,但領導像先看出來,只說多想想老人,多想想她們。那您的意思是我在一家里待的時間過長,其他的沒有兼顧……領導笑著送林仁出門說,我說的是全部的老人。 林仁挨個給區中老人掛電話,輪到寺忍家是第二天的十點鐘。打過去幾番是空音。其他老人除了一位長居外地暫回的托他捎來魚網外,都安安靜靜的在家里,正看電視,或閱讀報紙,他逐一詢問門口一鍵靈有無失靈現象,這周兒女能否按時到家,窗外魚池這兩天積雨太潮不要清理后,決定先去趟寺忍家,然后再給他買魚網子,幫她換魚水也來得及。 他没想到就在那天,寺忍第一次承认听见了铃声。他站在门口,已经等了一会,终于等不住,他开始又害怕了,责备自己怎么这样幼稚,上前急匆匆推门,他也想好要是实在它不动,那他就报警,但门开了,他更加苛责费去的这段宝贵时间啊,他慌里慌张连门没带牢就进去小门廊,果然,这里应该有寺忍为客备好的鞋子不见、鞋柜四敞没有了鞋。他摸着墙木边步子踉跄颠波,跑近厨房,水池里都是碗;到小厅,一束干茉莉,一把剪子,花丛拨弄得乱开,碎花子撒遍木桌。他这才想到先去卧室該看一看,林仁意识到什么,脚步不再忙乱,沉重地拖行,心里悲伤,转过小室墙角,他落一眼,寺忍房间空空如也,这是他第一次到主人卧房。他战战兢兢地一点点靠,眼刚张见木条绷面的理橱边,那只熟悉的浅灰布绣鞋底朝他橫著,林仁一步迈进来,寺忍头冲从窗射进的晨光,银灰头发很安静,盘高的部位压進地面,静静的一种撞倒的姿势,躺着。他不敢快走,轻轻地准备接受,来到身边,手慢慢地伸,寺忍鼻子马上接触到这手時,她醒了,他吓的直接坐在木板地上。 她醒了以后觉得自己样子不好,接着就要起,他才反应过去,扶住她肩头,她笑了。缓缓地,她撑一手,边端详身上灰丝睡袍子,不好意思了,我,这是昨晚上,弄花来着。他没觉得别扭,只是眼光稍错开,发现她灰丝绸近摆地方,忽然很亮,他头再往这挪,原来这里是昨晚的灯,亮到现在。寺忍觉着,人没全起来,转身也看灯,那是盞吊花灯,一根曲里拐弯的黑铁镂成颤枝子,来到顶托坠个倒钟,花皮子圣白,底边波浪延展,里面朦胧间有个灯泡。这也是孫子的呢。說完她就完全起來了。 從這天以后,他和她關系更能進一步,常常,不是他偶然來到飯點,就是她主動邀請他留下順便吃個晚飯。他也漸漸和她談得廣闊,某些過去不敢問想提的事,他都不用事先做鋪墊,有時她或忙盛飯,或正看窗外,都會直接接過話來。有一天雨說來就來,他和她相談投機,聽見雨聲,那都已是雨后。他想起看眼窗外的時候,不是暴雨,而是狂雨了。雨一直不停,從窗框上連續猛烈地刷,灌到窗底,雨柱變扁,桂和榕樹的輪廓拉圓,綠樹冠子掉下來,膩在赭樹干,灘了一地。他想到那天晚上,寺忍看燈,神態和詳,話里很靜,她半臥身子前見過燈,林仁琢磨,那個晚上她聽到鈴聲。 我今天早晨天剛亮,好像聽見一串鈴。林仁耳朵瞬間失聰,如瀑的雨聲消失不見,他轉頭過來,眼里裹了點淚,寺忍顯得寬胖,頭很小,身子巍巍然在動,他眨巴眨巴,她坐在原地,沙發周圈沒有一絲折皺。啊?他聽自己的聲音問。寺忍笑著回了頭。屋里一人安坐豆綠沙發角,一個蹭了半邊椅子,倆人之間,巨大落地窗子的淺藍布簾拉緊,中間環條起個金勾,吊掛墻角。嘩————!林仁耳朵噴進雨聲,外邊大雨依然如柱。他想問她剛才是不是他耳背,還是真的聽見從寺忍口中終于說出鈴聲,但轉而覺得在這雨天計較,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林仁繼續喝進茶水,窗邊近處的寺忍摸了摸袖子,偏頭說給他把窗子簾關一關,就起來身子,走到窗戶。 這雨后還是雨,真大。接近尾聲,風忽然起了。榕樹蔽天葉子亂舞動,最近的枝杈相離,劈到馬上爆裂,最遠端的葉子又婆娑厘回,和青黑天際的榕葉纏成塊,風撕裂它們,嫩莖粗紫莖跩開,迸緊到最后幾片,片——!剛掉落的綠茸葉,震到風團,翻了幾滾,連同些老葉,刮遠了。你看,這么激烈,一點聲音都沒有。他聽見她這樣說,繼續看著茶水,沒接什么。和我一樣,都老成個妖精!這么長一會兒讓你呆著,也沒個話兒。林仁驚地抬頭看窗,剛才您不是說…… 寺忍想到回來,雨已經馬上要停,稀稀瀝瀝地下,敲打矮寬的桂樹,沒看見寺忍什么時候開了條窗縫子,一股雨后濕泥夾雜柏的清香吹下窗子。林仁想她真是怪人,這么久就讓他聽,卻一點他想聽見的事都沒有。他把她想成老人,低頭看看表,已經六點了。坐著拽了拽上衣,寺忍從廚房里走出,端上熱乎乎的鴨子湯。今晚上你要放心,就留在這一晚上,看這雨再下。林仁接過小海棠花碗,喝著濃湯只是點頭。他想明天終于能讓領導放下心,不然還真擔心這種突然的天氣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林仁看著寺忍精心準備的被褥。一大朵一大朵藍色的雛菊瓣子,盛開在下雪的地面。他悄悄鉆了進去,頭靠上床頭,曲高膝蓋,手摸著摸著很柔軟的被面,想到寺忍,怎么這幾次要問她孫子回沒回來倒忘了。嘆了氣,提醒自己再怎么明天頭一件事要記得問,伸手拉動燈繩。 夜氣降下了,雨后的夜,潮濕,百花的香氣在屋子繞來繞過去。延到小客廳,一張寂桌,倆棵干梅花,窗下空空的沙發,三個鑲玻璃的高柜里,那幾張相片更改了位置,靜靜地擺在一小叢瓷質百合后。延近廚房間,長扁窗透來的迷藍光線,潲到倒掛的不銹鋼鏟子,反出去,打在窗下壁紙上臘梅花枝,一道碧綠映襯小花。寺忍睡著,床前燈調為暗度,花罩隱隱約約,她今晚蓋的,是六年前孫子特別喜歡的小藍花被。林仁半睡半迷糊,有幾次夢叫醒頭磕了桌子邊,眼睛睜不大開。花氣分開了,一半薔薇跑到小倉,外邊倚墻的木幾上電話也像睡著,安安穩穩。一小陀玉蘭萎萎叢叢,停到廊子,靜了靜,就來到了大門邊,由門縫滲出,擦過鐵門欞子時掛點。 “鈴——!鈴!——鈴!……” 他先驚醒,他去听下个错层睡着的寺忍,咝咝的呼吸声掺在震耳的鈴子里,他想想还是捏手捏腳披上倒衣服,袖子耷拉着腰,下床小步小步往前擦著地走。他先是感覺在小廳,到這,鈴聲低沉,逐漸遠離房子。他再來近廚房,鈴一下子滅了,留下阵回声,使他感觉还有,扶著冰涼飯臺打量周邊。他猶豫著原路退回,貼着墙倒走,他看到自己袖子鉻了個藤花影,透過磨砂窗,鐵門外月亮升上來了,他感到奇怪,白天看上去模糊的樹,這會兒都很清明,他甚至看出哪棵是桑,那株更遠些的高芭蕉斜上是個滿月。他再低頭,鐵門上鏤花影變長,他意識到自己一直在走,外邊的樹,葉子靜止,忽遠忽近,更像每一步逼近他向這來。藤花再看不見時,他整個身子融進桔黃色,想到腳下已是寺忍房間的過道,廊子右墻上篩出個拱窗欞,她屋里的燈亮了。 盡管還是怪異,林仁盡量讓自己馬上恢復神態,因為他不能不比老人,此刻,寺忍頭面順潔地半坐在被窩,下半身雖是在被中,但仍是和詳高貴地注視他,浮上微笑。 睡不著了,也?林仁滿面慚愧,在個陌生的老人房子,半夜像鬧鬼般倒穿衣服,轉完圈發現還是自己多疑,再副怪相站在人前,對方非但沒有詫異,反還那樣慈詳問候,自己看著半個倒鐘衣,倆個袖子快及地了,只有笑笑,最后還是寺忍讓他進屋,問老站外邊那不冷么,讓他好不容易抬著頭進了來。進來后只坐離門近的椅子,椅背上搭件兒童絨衫子,林仁身子一靠,閉住半袖轉頭。哦!這是我孫子的。這也早不穿了,告訴拿他那不聽,一放就是論年。林仁忽然問寺忍您這夜坐著要不看凍著,我還是回屋。寺忍光笑著指指窗子,一面粉紫簾子捂得嚴嚴實實,我這個是絨的,隔涼氣!再說我想給你說說,剛才。 剛才?他本來想問那個第二天的事,被她先說很吃驚,這么說她一直也沒睡著,或者……是這回真的聽到了鈴聲。剛才我……說到這他又怕嚇著她,咽回去了,啊剛才我有點口渴,到廚房接了點水,窗外月亮有了,惹得我看了會,挺美的。啊,月亮啊,嗯。寺忍意味深長地注意地板說。說起月亮,這還是除了我孫子陪著外,你是第一個愿意下完雨的晚上陪陪我這個老媽子的好人,其實我每天都能見月亮。我記得我孫子說他只要以前一來,都是這種月亮圓起來的時候,有一回啊,他來得早,讓他爸爸叫回去的也早,沒趕上滿月,他爸爸倒是欣慰,以后總在節日里說亐得他心細,要不就對不住我。那孫子是不是不高興了?林仁聽著柔和,想到哪問哪。我孫子可不比他爸爸,雖是我兒子的兒子,但最疼我的是他。他不但不很高興,而且從那回以后見月瞅著近弦月一盡先就來看我,住上幾遭,有時光晚上,白天見不著,嘿也不知道他這個小子跑哪去玩。哦……林仁看向天花板,默默點頭,寺忍影子蓋上他的簾子頭,他覺得也不像她孫子和她說話么?我孫子他人長得美,長得安靜,真不像那張照片這么呆滯。有過這么一回,他就在放干花的小桌上寫字,夏天快完了我縫著個褲邊,窗子就來了片彩云,我手頭上的褲子溫暖,手指尖有光,重影,長指頭落在玉色褲腰,黑蜓子稍一高,牽上些土,底下玉茸茸的,也漿上來末末,覺得一下子有好多人看我,眼那都舒心,我在高樓上,緋紅、淺紅、輕紫、絳色一輪輪滑過手背,我在個瓦檐殿上袖東西。接著想到身后小人,他半臉隱在頭發,長黑睫毛撲撒撲撒,黑眼珠靜靜的,上寬下窄的臉兒,一動不動,我真喜歡啊。 嗯。瓦屋頂子上的人,我也知道。寺忍還是向燈,笑著。然后她說你閉眼,嗯,閉上。林仁看她身上裹得被子嚴實,放心地向后,靠在長背椅子,就閉上了。倆人不吱一聲,表從一個方向卡嗒卡嗒響,他終于想起那個座鐘,這幾天了,惦記著寺忍,也沒去注意它到底是停是走。表針卡——嗒——卡——嗒!卡……嗒……卡嗒………………下個斷點比上個沉重、凝塞,聽著,像不走,嗒越來越緩,跟不上卡,然而是錯覺,嗒聲從不漏,太過留意,卡后邊是嗒,他擔心得過了。他想到家里,鐘一圈轉一圈,一輪快一輪,時間在原樣前進,鐘時比八點進九點,比六點快七點,比十一點到十二……人生加速奔進,快速崩塌。它兢兢業業走,有個小人住里邊,指示它,錯誤的開始,錯誤的進程,即將錯誤的終點,它都在拽,在飆,漫無目的、無始無終、有始有終、卡嘣劈掉。 瓦檐殿清明,下家是花頂子,我啊,就在個二層還是三樓,右首啊,有個標桿,飄飄著落山太陽,我手針子前邊,是撮子干花,雜花,半死的苦瓜秧子、一根根兒串紅、有模有樣兒的枯櫻花子,啊哈……透太陽里邊,我站的地兒又高,斜陽子落我眉頭,我眼睫毛光閃,一閉上,那顆顆子梅花就紅了,我一睜,它沙霧楞楞地,哎?是黃的!嗯……!我就看遍繡邊,所有梅花樹有陰影的,有正沖太陽的,落下去的大太陽。淺的、酸的、慢的,我深吸口氣啊,就老想好像以前些沒辦好的事兒,現在都不要緊了,我老覺著這時候啊,窗戶外頭,有人,有一些人,也覺著我很好,是個好人。 林仁來到段回憶,為記下個句子,來到大窗跟,四點太陽柔和,穿墻越戶,他寫字本上耀了一片,都是霧黃,他手不停,一筆一劃寫舊亭臺。外邊廣場小兒叢躍,呦嗷沸天,他眼前也多花,絡墻的干藤子,他感到幸福。睜開眼,寺忍就在這時不再說話。 林仁回到屋,想剛才給寺忍掖好的被子,外邊就刮起大風。他又想到每回打字踫上預警,出一個章丘大風速報,他老笑怎么世間的風也有命名,這一塊就是章丘大風了。單獨墾出來,一個獨立的時間,一個小世界。他縮進被子,看天花板,這屋今晚窩在大風,也像個擱來的空兒,里邊就是林仁和寺忍,沒有其他,過去的人,將要來的,都不算。半夜,大風鼓動的鐵門響,咣當——咣當!后邊的木門也扯,像有個人費盡心神,見老想見的人。鐵與鎖在抗,有幾次他聽出馬上要斷,要不要去看看,他半睜睜眼,混里混沌里聽到嗚……嗚……里有個金屬聲收尾,鈴子隨風聲,一番揭地撩葉的轟鳴聲壓過,鈴也驟巨,滾進風團,最后幾個鋸齒般拉散開,風沒了,那陣回音一磕磕斷掉,卡在他心尖。他猛地醒了。 他大風里胡亂穿衣,總像有事要發生,心頭呯呯,他決定先去看寺忍,然后去看大門是否那根本不是夢,它就被風冽開。寺忍安然睡著,但呼吸得去辨別,因為每次巧被表針響蓋住。那個鈴聲堅挺,間隔的時間短了。仿佛催促,又像招喚,他跟住鈴,向前經過地板廊子,廚房,聲音沒了,他有點害怕,不再走,視線剛及黑黑小倉,鈴————!刺進耳朵,他扶住墻張大眼,見進門靠右,他總端詳的高木幾上,那臺黑色電話很安靜,他一步貼一步蹭地過去,他發現他抓起聽筒來了,鈴……鈴——!鈴……鈴………………!尖銳冷礪的鈴刮刻隔膜,慌亂中丟掉話筒,摔進槽口。他聽出聲音從大門那里,一聲闊及一聲。他離窗門只差一步,放鞋的錯層臺階樹影閃蕩,他再看窗,黑藍底里棵棵墨綠色的樹,張臂扯干地朝他奔,一棵柳枝子上天,漫天窄葉子甩到窗戶,一個粗壯的藤鞭子咣咣地揍玻璃,呼嘯北風呼應,卷高松針,倒豎著嗶嗶砸到半窗。在中央,他好像聽見鈴,他又感覺是風,游疑不定,當鈴大響,樹叢亂顛狂,鈴一消失,葉靜下,等待不過秒,鈴再次響動。 他看著,一眼不錯,出了個熟臉,像在哪見過,仔細打量,又不認識。每當有鈴就張大嘴,樣子就不像小孩子,林仁退后一步,端詳。 這夜風一刮連陣,大約天亮后停住,林仁下床先去看寺忍了。 直到有一年,林仁想家里座鐘后,再想好人寺忍,就不再怕那個窗戶外邊的小人。他終于記起,曾在張相片上見過。座鐘無故跑快的事,他也不瞎想是逼人,有些事根本沒有這么懸,但只要寧信,誰都不敢說沒有。然后他每年都去寺忍墳上獻臘梅。